藝術家簡介

陳為新,福建省羅源縣人,1992年至今從事壽山石雕刻藝術逾30年,師從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潘驚石,先后被授予福建省工藝美術大師,福建省民間藝術家等榮譽稱號,系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,福建省第五批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,高級工藝美術師,一級/高級技師。畢業于福建師范大學雕塑系。
多件作品被國家級、省級美術館和博物館收藏,現任中國壽山石文化發展研究中心副秘書長,福建省民間文藝家協會青年委員會主任。為進一步推動壽山石印紐雕刻文化傳播,對非遺項目進行保護傳習,于2021年初在三坊七巷區域建立300平方文化場館“為新印紐藝術館”。
作品解析


《羅漢圖》這組作品,其靈感來源和語匯的參考都來自石濤的《百冊羅漢圖卷》,這套圖卷的資料,陳為新最早得之于2011年前后。當時此書所公布的這一石濤羅漢圖資料是此前從未問世過的珍品,紫禁城出版社和榮寶齋曾聯名為此書主辦活動與發布會,收藏界一時間人人側目,書籍出版,立刻一卷難求。陳為新費勁周折,才得到這一圖式,并開始了長達十二年的鉆研和思考。
這套作品并非一般明清壽山石佛像中獨立陳列式地呈現,而是更場景化——羅漢們被安排到了具體的一個情境之中,他們本身的形象都不是孤立,每位羅漢都神情不一,或微笑、或好奇、或微微抬頭張望、或凝神思考,神態各異,豐富的肢體語言與生動的面部表情,把場景的建立變得更有層次感。這對于此前專攻印鈕雕刻和傳統雕刻研究的陳為新而言,是一種啟迪。經過數年的揣摩、醞釀后,他開始著手向從未有師承的領域摸索。
“我從1992年開始雕刻,就是學習獸類、印鈕的雕刻。可以說,離人物圓雕都是很遙遠的,但三十年來,為了研究明清古典技藝的復原,我走南闖北。這段時間里,不但見到了古典的壽山石雕刻,也見識到了不同領域的表達。其中古典的繪畫對我沖擊尤大。”
“壽山石雕刻里,當塑造的主體不是動物的時候,則它們的形象大部分完成的是裝飾效果,有些則被用來作“俏色雕刻”,也就是創造一個視覺的焦點,刺激大家的感觀。小型甚至微型的壽山石雕刻體量有限,獸的元素就經常是工具化的。鈕雕更是如此,獸刻的大,人刻的就小,總而言之,重心只有一個。但是在我看到這套羅漢圖式的時候,我感到一種獸和人共同構建畫面的可能。這很有意思,在石濤的筆下,獸不是陪襯,它有時候和人是平等的,也能成為場景的核心組成部分。這種新奇感,也是促使我從原本的領域突破,開始創作人物圓雕,以及繪畫式、場景式作品的最初原因。”
《羅漢圖》中《白象聽經》這一作品正是在這種趣味思考后,不斷錘練所得的成果,在這件作品里,羅漢們有的三三兩兩交談,有的張望四下、有的冥思禪定,還有侍從、番奴、動物、異獸等委身在羅漢們身旁。而白象沉靜的神態,則成為了他們之間主體性最強的形象,將所有的羅漢關聯了起來。雖然是羅漢們的聚會,但“象”也是他們中的一員,它不被邊緣化,反而被中心化了,這個形象成為和羅漢們一樣重要的角色。
這就是非常典型的“石濤化”的處理,也就是對于場景中異獸的擬人化處理。這種擬人化不僅僅是在神態上,也在眼味、五官的結構安排上,有些也加入人類的造型元素,使人們很容易發覺它們不同于常物的,類于人的神智。
陳為新的這種“石濤法門”上的偏好,在另外兩件作品的異獸開相上表現的更為明顯。它們有的似在好奇地探究羅漢的所思所想,也有的似乎本身就因聽法而心有所感。
在過去,陳為新的雕刻中大多數去追尋動物性的神態,這令他的作品得到寫實上的助益。而這種擬人化的塑造,則是一種反向追尋——自然的獸性雖然被削弱了,相對而生的靈智卻被強調了出來,它們也成為了一種“人”的形象,共同完成了畫面的焦點。
在雕塑化傾向更強的中型圓雕作品中,這樣的安排更能使人們感受到工藝的趣味性,降低了對于觀察時間的門檻:開宗明義,一目了然。
其次是質感上的營造,眾所周知,石濤的作品石以線條的駕馭聞名的。而很難想象在雕刻中,塊面作為首要表現形式的情況下,“線”的形態和走向要如何來表達。
陳為新的思考答案是“以面定線,以線協面”,譬如使用雕刻去在線羅漢們身上的僧衣似乎十分簡譜,但實際上有大量的衣褶刻畫,其隨各類姿態,有大量的走向、陰影上的構型難度。羅漢身著的絲質袈裟在石濤的繪畫中,往往通過細勁流麗的線條,勾畫得華麗而又繁復精致,這種線條的使用,旨在令袈裟展現出輕薄而又順滑的質感,即所謂“天衣”一般的視感。
在《羅漢圖》中,陳為新為完成這種“飄然”“貼裹”“順滑”的形象,取用了民國時期,福州地方壽山石雕刻“東門派”名手林元珠所常用的技藝手法。
在《羅漢圖》的三件作品中,羅漢衣褶線條均以快面的交疊來“搭造”出線條。也就是說,兩個甚至三個面交匯的情況下,才會產生一個線條。有些交匯面會因為造型產生光影上的區別,這使得人們在觀賞時,會產生視覺上的錯認,從而讓線條的指向性變弱。
為了使袈裟不像是僵硬地套在羅漢身上的,而是更像是貼在身軀上且隨時會流動一樣,似乎在羅漢們都揮手移足間就可以翩翩而動,陳為新數次改塑泥稿,以確保最終雕刻的產物,能夠在不同方向、強弱的光線下,都能呈現出最佳效果。
除此之外,另一種來自石濤的啟發在于對獸類毛發的雕刻。石濤擅長使用淡墨勾勒異獸的須毛,使用線的組織和層次變化來表現異獸的毛發蓬松柔軟的質感。陳為新在雕刻時,運用的是一種更加精致而細膩的雕刻法,也是他從多年古典壽山石雕刻技法中領悟出的“流水絲毛法”,以小塊面堆疊和古典開絲技法交錯使用,讓異獸的毛發千絲萬縷,層層疊疊,出現一種交織纏繞,松而不散但狀態,來模擬“墨”感,最終雕刻出了《法慧無窮》中的異獸重毛被身的形象。
這種質感上的營造,能夠最好的再現出石濤繪畫中“筆意”的部分,但實際上的技巧運用,卻和繪畫大相徑庭。
陳為新認為:“中國畫中,線條不僅是對外形的塑造,同時也是對表現對象的內在意涵的表現,塑造形象的同時,還能傳達情緒。畫家通過線條的粗細、力度以及節奏變化等來造型,不僅是對人物外在形象的展示,還是畫家自身情感的一個展現過程。繪畫的人怎么理解眼前的東西,就會使用怎樣的線條。在我們壽山石雕刻里,這樣的情況也是通用的。”他補充道:“羅漢是一種瀟灑、自在、智慧的形象,當他們被放在一個交游或冥想、聽法這樣具體的場景里時,僧袍衣褶的刻畫就是對他們情緒的刻畫。只有面目、神態是不夠的,肢體能補充一大塊的信息,然而對衣褶質感的呈現,才把這種不受束縛的情狀補完。”
“人們看到這些僧袍會感到松弛,這些僧袍不是厚重的、拘禁身體的,它們讓羅漢看上去自由自在,人們看到這樣的場景,就先放松下來了。衣褶是我們最熟悉的生活細節,什么樣的服裝材質有什么樣的穿著體驗,看到人不需要思考,馬上就能憑借人人都有的生活經驗理解這個場景。這就是塑造質感的關鍵,不僅是為了寫實,也是為了讓大家更簡單地享受到作品傳遞出的氛圍。”
“動物的毛皮質感也是一樣的,當動物生活在自然環境里,它們的神態是戒備的,緊張的,從皮毛的狀態都能看出來。野外生存的動物,時刻需要躲避天地和攻擊捕獵的,它們的毛發很難蓬松又豐厚。須毛茂盛,是從容而有余裕的動物才有的特征,強健的軀體不用特別刻畫,皮毛的狀態就能引導大家聯想,理解了。因此對須毛的質感營造,也是這些超脫一般生物規律,產生智識的異獸形象的一部分——從容的境況才能像人一樣思考。當動物像人一樣思考的時候,它們成為畫面焦點的核心組成,就非常自然而然。它們幾乎和人沒有分別了,只有軀殼形式上的不同。這也是佛法的理念,精神超越身體。”
“對于古典雕刻技藝的復興,是追究技術、技巧和造型方式的過程。了解這一切后,‘古意’‘畫意’的汲取才是更為重要的。”
“這套作品,幾乎是從全冊幾十個場景里雜糅出來的,在創作出來后,大家會問我:怎么看上去覺得既像這一張、又像那一張,但實際上又都不是呢?”
“我的回答是,因為每一張羅漢圖都是這套作品的養分,但它們不是任何一張作品的原樣臨摹。作為創作者,我們自己的作品,應該是一個時代特征的反映,也要體現個人的精神。雖然這套作品,以石濤的筆意、造型和元素作為繼承的基礎,但學習古人不是一味地摹古,而是融各家之所長,取其所需,再在此基礎上,加入個人的理解。擁有這種自覺性,才能展現出更多的創作趣味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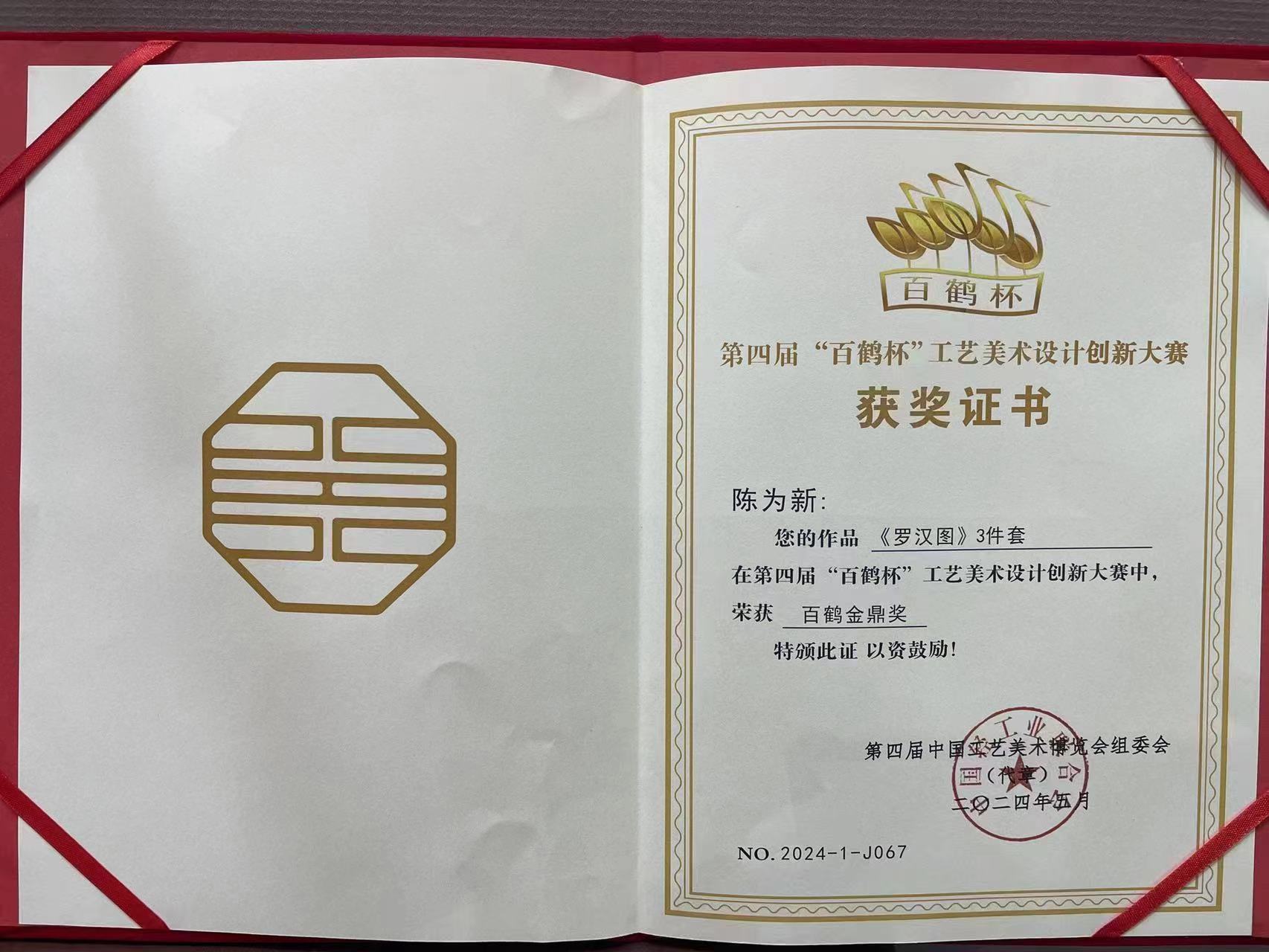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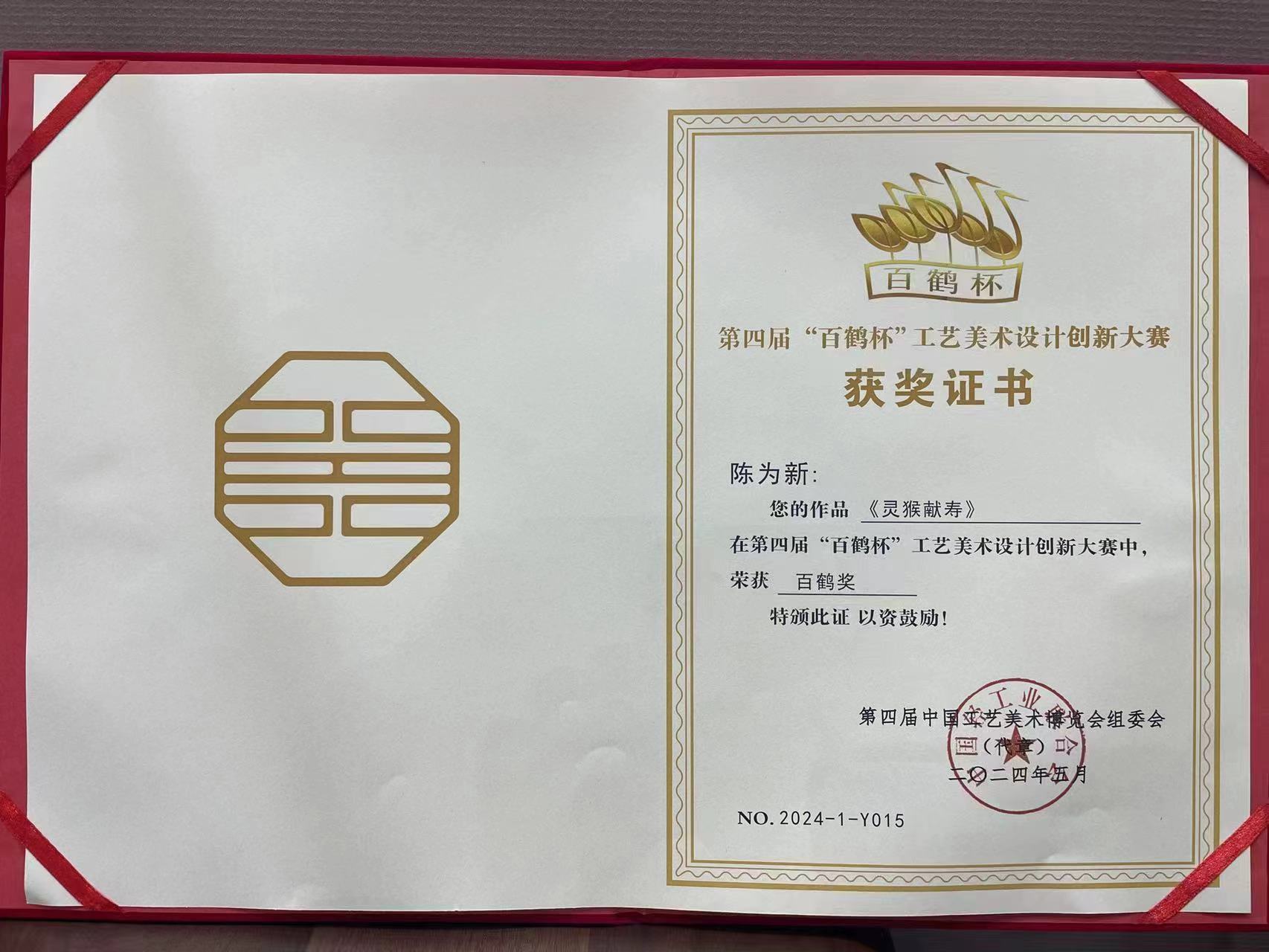
作品欣賞








(內容由藝術家本人提供)